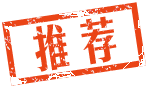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梅朵 于 2015-11-17 09:15 编辑
梅朵前言:
偷得浮生半日闲,再来读几段文字。许冬林的文字虽然精美若爽口的甜食,但吃多了也难免有想换换口味的冲动,当代散文女作家之中,也久闻雪小禅的大名。
雪小禅,知名文化学者,中国作协会员,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读者》杂志百名签约作家之一。(百度)
复制一段有人评价雪小禅的文字:雪小禅的文字,适合在慵懒的午后,抱一盏清茶在手,静静地去品读,她的文字中充斥着怀旧色彩,像一副雕版老画沉淀在岁月里,华美的色彩中折射出一份清冷的感伤,有一股轻薄如烟,淡然的惆怅,美得蚀骨。她的文字,如她的名字一般,有一份剔透的清凉,微微地触动了心。读雪小禅,应该说,读的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份心情,她的文字,极像一个面目文雅的女子在岁月的一端,渺渺地掀开一段令人心碎过往,让人读得怆然泪下。
先读一篇”无量悲欣“,来细细品味一下她的风格。
无量悲欣 雪小禅
弘一法师在福建泉州圆寂前,写下“悲欣交集”四字,字字骨力。早已无法用书法来定度来横度,他连人书俱老都不要了。
大师林风眠,那个八岁拿着菜刀去救母亲的孩子——因母亲私通要被族人处死,头发上淋了油,然后即用火点着,他拿了菜刀冲进人群救下母亲。那八岁的悲欣与交集。
晚年,他客居上海,闻知傅雷夫妻双双殉梁自尽,他把自己珍藏了多年画作扔进浴缸,用水泡软,然后再淘成纸浆——那是他毕生之心血,比之当年他从重庆再回杭州艺专,看到自己千山万水从国外带来的油画被日本人用马蹄踏,他的心更痛。无所谓悲欣矣。他把纸浆一勺勺舀到马桶里,然后摁下开关,冲入下水道。那一刻决绝与麻木,绝望与凄凉,已跌入无量悲欣。这是文革时期,林风眠心如枯木。
晚年他移居香港,再没回来。这个20多岁被蔡元培任命为国立北京艺专校长的天才画家,一生颠沛流离,我常常在西湖边他的旧居里发呆,那个隐藏于山水树木间的二居小楼里悬挂着他的画、穿过的毛衣、躺过的床、用过的画案。
他在风中睡着了,他是风中的小鸟。
少时,我听林徽因、徐志摩、陆小曼的故事。只当是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好事者写林徽因传,或拍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均是拍的情事,于今日来看,格局甚小。
回头再看,不再叹志摩三十六岁命丧黄泉——他早死早托生矣。
晚年陆小曼,牙齿掉光,头发落半。当年的绝世佳人沦落到用蝇头小楷抄写《矛盾论》,岁末被评为“三八红旗手”,她画画写新生:年底更识荒寒味,写到湖山总寂寥。她29岁之后的生命毫无意义,残喘到支离破碎。人世间冷眼悲欣尝尽。天注定。
从前对林徽因的认识颇曲解。自以为要活到任性如陆小曼敢爱敢恨。但中年后愈发欣赏林徽因——坚韧饱满,如一粒坚果。生机盎然却又凛凛飒飒。徽因先生,我懂你晚矣。
是她出于对建筑的挚爱怂恿梁思成去学建筑。是她,在抗战时期,与梁思成坐着驴车走遍中国万水千山,180多个县,八千多处古迹——头上是日本飞机轰炸,脚下是被焚火的横尸遍野。他们测量、绘图,在长途跋涉中,梁思成牙齿掉光,林徽因患了肺结核。
在李庄,儿子梁从诫问林先生:妈,日本人打进李庄怎么办?
林先生掷地有声:投江呀。
一个风花雪月的女人怎么能有这样的赤子之心?坐驴车、用脚量,他们画出了中国第一本古建筑的图案,还有珍贵万分的测绘数据。
当那些图纸被洪水浸泡时,他们痛哭失声。
拆老城墙。梁思成扑过去嚎啕:50年后你们会后悔,会知道错了,因为真理在我手上。林徽因拖着残病之躯去求:你们拆的是八百年留下来的真古董,以后再建亦是老古董......北风在号,他们在呼喊。没有人听。新中国建设如火如荼,林徽因走了。梁思成亲自为爱妻设计墓碑——这一生的风雨才是执子之手。年轻时的任性和风花雪月,如何能与赤子情怀相提并论?
梁思成晚年,没有欣,只有悲。他挂了黑牌子才允许出门,那上面写着:反动权威。他被领导红头文件批示:又老又没用,可以当反面典型。在最后的光阴,他只字不写,只闭目——他懒得再看这世界一眼。连无量悲欣都嫌多余。
年轻的马尔克斯在火车上读福克纳《八月之光》,赞叹不已。多年后写下传世之作《百年孤独》,晚年马尔克斯得了老年痴呆,家中物件俱贴上标签方才认得,标签上写上物品名称、用途。他不自知凄凉满怀,却早已凄凉满怀。
夜读孙犁《老荒集》。真是又老又荒。在给贾平凹的信中他写道:今年天津奇热,我有一个多月没有拿过笔了。老年人,既怕冷又怕热......那是1983年7月31日,那时贾平凹刚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他告诉贾平凹:写些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在《吴趼人研究资料》中他只写了一句话:此书字太小,不能读也。我也已目力不及,感同身受,字太小便不读。
年轻时孙犁这样想:我一定老死故乡。不会流落外地的。但他终于离开了,再也没有回去。
T跟了我几年,见了世面,仍然朴素干净。一日看《舌尖上的中国》演到山西面食,她泣不成声。我每见山西二字亦想到她的阳泉。甚至听到山西话也格外亲。她亦不知道我每每写她、她的母亲、H四人闲聊、吃饭、喝茶时,已是捧着银碗盛雪时光,珍贵得连痕迹都美。
乡下表妹仍在杀猪。每日五点起来杀猪。她说,“我听到猪的嚎叫便心疼”。但她育有二子,要上学、吃饭、花钱。她只能杀猪,只会杀猪。
暮春时节,随母亲扫墓回娘家。母亲思念外婆,每忆便涕泪,有一段时间眼睛都不好了。这次回去看了二舅母,她更瘦了,穿了去年旧衣,照看着四个年幼孩子,还要忙活家里的农活儿,眉目间少有欢喜。母亲塞给她钱,她便蒸了手工纯碱馒头,又炸了许多油饼让我们带着。那自然是民间仍有的质朴情义。母亲说接她城里住几天,她说可不行,四个孙子没人看,地里的杏花也嫁接授粉了......似水光阴中,没有惊天动地,皆是无量之悲欣。
晚年林语堂客居美国30年。他定居台湾阳明山上看着他的家乡漳州方向,老泪纵横。那时正文革,他家园不能归,只有望乡泪潸然。翻看《生活的艺术》和《苏东坡传》,想与这些老人秉烛夜谈。
一日父亲和母亲说:你若有一天离去,我不哭,拉二胡曲给你听。母亲便生气,说父亲心里没她。父亲读庄子多,知道庄子丧妻后击鼓而歌。生命的逝去原是天地自然。祖父去世父亲便不哭,也拉二胡曲。众人皆笑他痴,我却明了父亲的无量悲欣。
春日一个人行走风中。见众人皆碌碌。二大街上的饭店关了旧的又开新的,桃花、杏花皆已落尽。修车的师父满手的油在忙碌,水果摊小贩仍旧给的分量不足。胖姐的蔬菜店还那么热闹,聚众在那聊天的人有闲茶喝。
我去菜市场买了块猪肉。肥的熬了猪油,炒菜有植物油没有的厚香。瘦的剁了馅包饺子吃。今春的荠菜正鲜,我买了而今,用热水过了,然后一个一个包起饺子来。
梅朵小语:
忍不住拿雪小禅和许冬林比较一下:
同样的清高孤傲,同样的小资情调不同流俗,但美人千面,雪小禅的文字和许冬林的文字各有不同的美丽与动人之处。
许冬林的文字美在精致玲珑,又清淡萧远,如江南烟雨中村头的几树浅浅的杏花,水墨画般的朦胧又梦幻。雪小禅的文字美在摇曳多姿,又深沉内敛,如空山深谷中静静开放的几株幽兰,淡淡的散发着一种神秘的幽香和魅惑。
如果说许冬林的文字带有几分仙气,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纯净;而雪小禅的文字则带有几分妖气和鬼气,却又在不经意间带出几分禅气。比起来,雪小禅的文字包容量或许更大一些,却也因此略显隐晦了些,更需要细细的品味。
读完她的”无量悲欣“,我不敢胡乱评价,只感觉内心有百般人生滋味汇集在一起,弘一法师的”悲欣交集“该涵盖多少人生感悟和佛家的大彻大悟。
雪小禅避开了简单的道理阐述,而是列出了名人和凡俗人家的很多事例。无量悲欣是什么,是人生无法衡量也无法评价的那些悲喜苦乐,人生的悲喜常常无法用道德的善恶来评价,也无法用单一的价值来衡量,活着,有许多的不得已,不尽如人意。
读完此文,顿感薄凉,感叹一下雪小禅,这个把世事看的太透彻太清冷的女子!
但文字的最后两段却出人意料。
真正有生活智慧的人,从来不会因为世事凉薄而失去生活的希望。正如雪小禅的一本书的题目”在薄情的世界里深情的活着“恰恰阐释了她这篇文字的结尾深意。
生活,便是无量之悲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