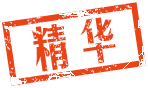那教室,叫一个小呀;那同学,叫一个多呀;那座位,叫一个挤呀。挤到什么程度?二张桌子五个人。话又说回来了,有得有失,不这样坐,我哪来那样多的同桌。
我的同桌,这次必须是个男的了:鼻涕王,邋遢虫。过去大家伙都穷呀,但衣服哪怕再破旧,也都算是干净的了。可是那鼻涕王邋遢虫的衣服,从来就不知道本色是什么。
那时,我是小组长,主要工作职责是收作业本。若是有哪个同学没有完成作业,我偶尔也老虎发威。上次有个同学没做作业,嘿嘿,我抬手就给他撕了!不过,第二天,在老师的教育引导下,在同学的哭诉威逼下,我老老实实地向娘要了几分钱,买了个新的作业本还他了。
鼻涕王家住城郊,有很多稀罕的吃食,山芋干、花生饼、芝麻饼,诸如此类。
这个山芋干,可不是现在超市里干净软糯的那种,就是地里直接起了山芋,用水胡乱冲一下,切片后扔地上晒干的;那些花生饼、芝麻饼,其实就是榨油后的副产品。这些,在当时,绝对算是美食了。你想呀,那时看到课桌缝里的一粒芝麻都想扣出来扔嘴里,若是来点山芋干、花生饼、芝麻饼,想着都要流口水了!
真是麻烦,我说是写同桌,咋又扯到吃上了。
书归正传。我是组长,这个同桌鼻涕王自然是我的组员。这家伙作业经常是胡乱的,偶尔是不做的。我也经常狐假虎威地扛着老师的旗帜来批评教育他。他总是就是擦擦鼻涕,继续我行我素的样子。
有天,下课后,他眉飞色舞地说起他家的大母狗生了一窝小狗,一帮同学听的那叫一个认真,扯着扯着,就扯到了狗肉了。那年头,家家都很穷,但也有狗肉不上桌的规矩,所以,城里的孩子很少有吃过狗肉的。
鼻涕王一定吃过不少的狗肉,鼻涕王自然成了大家羡慕嫉妒恨的对象。
在狗肉的衬托下,鼻涕王成了群体的中心人物,什么班长呀,班委呀,还有我这组长呀,全暗然失色。
在狗肉的光辉下,那鼻涕王说得更来劲了,他的一句话,触动了我。
他说:你们不知道呀,狗肉可是大补!无论什么病,吃了狗肉汤,全好!
那时,我娘病了,躺在床上好几天了。
幼小的心灵中,病和吃,又不得不联系在一起了。这还不得不说说其中的原因。
那时,大院里家家养鸡,自家产的鸡肉和鸡蛋,是饭桌上的必要补充。我就经常蹲在鸡窝前,守着鸡生蛋,然后掏出来拿给我娘,让她炒青椒鸡蛋。但我更想的不是鸡蛋,而是鸡,最最喜欢的是鸡的内脏。
鸡就那几只,想吃它可不是容易的事。但有个情况很特殊,想吃就吃,那就是病了。
若是晚上病了,那吃鸡最方便,鸡全在窝里,很方便第二天抓来杀吃。但若是白天突然病了,那可就麻烦了。
鸡是散养的,家家的鸡全在院子里散步找食,而且那时的鸡,很是厉害,你若是追它,它很轻易就能飞到高高的树上。为了防止它们乱飞,会把鸡翅膀上的羽毛剪去一些。但就是这样,刘翔来捉它也一样得出身臭汗。
记得一次中午放学后,我突然病了,我娘立即来到我面前嘘寒问暖的。我无力地半闭着眼睛,有气无力地说:娘,我什么也不想吃了……我只想吃那大芦花鸡的心……
我娘二话不说,挽起袖子,走到院里。我软绵绵地挪到门口中,观察进展。
我家那只大芦花正在院里玩。我娘轻轻走到大芦花旁边,弯下腰,突然加速,一下扑上去。
大芦花可不笨,这时被捉,必是血光之灾!它是玩命地跑,我娘是持续地追,我感觉我娘的大辫子都在脑后飘了起来。我心里在给我娘加油,差点忘记自己是病人,要一起加入围堵大芦花的战斗中去。
扯太远了吧。说简短些。结果,大芦花的心、肫、肝就装在一个小碗里,热乎乎地摆在我的面前。
骗你是小狗,我真不是因为想吃鸡而病了,我只是因为病了才想吃鸡。但是这样病的次数可能也确实偏多了些,直到今天我娘还说:你就是小时候吃鸡心吃多了,一肚子心眼!
又扯到吃了,这事闹的。书再归正传。
鼻涕王说的是真的假的呀?无论什么病,吃了狗肉汤,全好?我吃了鸡心后,病就好了,我娘若是吃了狗肉汤,结果应该一样吧。
拉过来鼻涕王,咬起了耳朵:把你家小狗抱一只来给我娘吃吧。
鼻涕王自然不乐意了。但我很执着。
是否有权力寻租的因素在里面,我真不记得了,可能是有吧,结果就是第二天一上学,鼻涕王真给我抱来了一只胖乎乎的才出生的小黑狗。
下课后,我激动地抱着那暖暖的小黑如同抱着一缸狗肉汤一样,直奔家里跑去。
我来到我娘的床头:娘,你把它做成汤吃了吧。
我娘怕狗,吓得直躲。
唉,我家大人不吃狗肉。他们也不愿意把小黑做成汤给我吃。没办法,我下午就抱着小黑来到学校,把小黑还给了鼻涕王。
前几天听一教授讲课,比我还能扯,一下扯出来十一、二种“商”,情商、智商、财商、挫折商、领导商什么的。当时我就想到了鼻涕王,那家伙,当年在学习上没表现出来智商,但他那样小就知道了和大家分享食物,甚至还计划让我分享狗肉汤,多高的情商呀。
不知道鼻涕王现在怎么样了,我想,他一定会很棒。他一定会经常西装革履、油头粉面、呼朋唤友地出入狗肉馆之类的好地方。
他也一定早就娶到了个漂亮干净的俏媳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