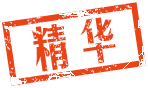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花落 于 2014-11-19 16:46 编辑
梁尘赞一声道:“好硬的屁股!”阿笑道:“好狠的戒尺!”说罢,提上裤子,拿了外衣,头也不回,径自向课堂外走去。墨玲珑也起身追去,经过梁尘身边低声道:“谁叫你个杀猪的来当先生,真瞎了眼。”梁尘闻墨玲珑身上有股幽香,当即识破她是女子,暗自好笑:我方才要使出第三刃,这苏阿笑就真成死猪了,日后你会知道是我有意饶他。见二人出了殿堂,往书院门外去,心想:此二人果然行事诡秘,倒要看看他们想干什么?当即丢下院生不管,自己也跟了出去。
且说阿笑步履踉跄,出了书院大门,墨玲珑从后面追上来问道:“阿笑哥,书院不住了吗?”阿笑道:“再住下去还不得被人打残。”墨玲珑道:“那你现在要去哪里?”不等阿笑回答,对面树荫下走出一人,代阿笑答道:“当然是和我回警署去了。”
二人抬头一看,来者正是黛簪。原来前日墨玲珑把阿笑从酒楼带走后,黛簪嘻哈鬼新娘三人商量,决定分头去找,料阿笑跑不出多远。此外三人本不是一路人,因救阿笑相识,如今阿笑走了,三人也匆匆别过。
黛簪沿途打听,终于有人记得阿笑长相,说他和一女往东边去了,黛簪便一路向东寻了,来至鼓山,此时二人从书院出来,让她堵个正着。阿笑身上没钱,正想让黛簪雇辆车送他回福州城,等到了城里再寻个机会逃脱,主意已定便坐在地上耍赖道:“好啊,我刚又被人打了,现在一条腿麻了,走不动路,除非你背我去警署。”黛簪道:“我雇辆车载你去警署,腿打瘸了好,省得你再乱跑。”墨玲珑道:“凭什么他跟你走?”黛簪道:“我这是例行公事。”墨玲珑道:“既然这样我也随你们去,我证明阿笑哥不是坏人。”此时梁尘走上前道:“这苏阿笑今日扰乱太学,我也正好去做个证人,告他破坏公共教育。”黛簪见一英俊男人,也掺合进来,便问墨玲珑道:“此人是谁?”墨玲珑道:“是书院的先生”黛簪笑道:“阿笑你真是四处惹事,还嫌得罪的人不够多吗?”阿笑道:“不是我惹事,是倒霉事情总让我碰到。我现在走投无路,正想去监牢里清净几日。”黛簪道:“要是认定你没有嫌疑,监牢也不留你。”
三人说罢,雇了三辆马车,黛簪与阿笑一车,阿笑屁股痛,只好爬在座上,其余两人各乘一辆,往福州方向而去,路上颠簸,阿笑一路痛叫不止。
话说黄昏时三辆车进入城里,行至三坊七巷,阿笑见车到吉庇巷,想起“熟肉离锅”的典故,心中暗道:此时不逃,更待何时。诸位看官须知,这吉庇巷原本叫急避巷,相传宋时有一寒儒,向屠夫老婆借肉祭灶,却被屠夫知道后,赶来将锅里的熟肉捞走,并出言侮辱,后寒儒考中状元,衣锦还乡,将屠夫杖毙,此后邻人见他,都急避而走,故此巷得名急避巷。
阿笑借口小解,遁入茅厕,黛簪墨玲珑让梁尘入内监视,梁尘推说君子洁净,不入污秽之地,死活不进去,三人在外等了半个时辰,仍不见阿笑出来,让赶车的进去看时,哪里有半个人影,原来阿笑早就翻后墙跑了。黛簪大怒,对梁尘道:“你一个大男人,进个茅厕都嫌脏,如今走脱了嫌犯,要是找不来,就以包庇罪告你。”梁尘心中苦道:我和你们一样也是女人啊。表面上只好道:“我今晚一定将阿笑抓住,交还给两位姑娘。”说罢三人分头去找。
且说这阿笑脱身之后,第一个想到的去处 ,竟是下杭街的杏花楼。阿笑自打来了福州,每日午睡醒来,先去烟馆抽鸦片,晚饭后与人看戏赌博,赢了钱就夜宿杏花楼,烟赌嫖这“三纲”是每日恪守的。这几月做了和尚没来,一旦脱去僧衣,便恢复往日行迹。
话说掌灯时分,状元弄的杏花天好不热闹,且不说堂子里香罗粉黛,红袖招摇,就连门外也到处是流莺,见到男客就往深巷里引。附近夜市繁华,各种鱼丸摊,索面摊前围满食客,直要到夜里二更时才歇。一般客人来杏花天,都从正门进入,只有少数贵客和名妓知道,楼内其实另有暗道,直通星安河。
此时正有一条小船,泊在星安河边,从船上下来一黑衣女子,从暗道进入杏花天。她进到大堂,把外衣脱下,搭在臂上,缓步上楼,招来不少男人目光。只见这女子:身材瘦削,体态风流,星眸含露,摇曳生姿。莫说客人不识她是谁,就连老鸨也不认得,问相帮才知道,此女叫柳暗殇,说是许营长叫的局,老鸨低声骂道:“哪里来的野鸡?又来占场子,给我盯仔细了,如许营长不来,就趁早把她撵出去。”
柳暗殇上楼,进房等了一会儿,见约的客人还没来,就走出房间,倚栏而望。阿笑偏偏这时进门,许多姑娘都识得阿笑,纷纷上前招呼,说笑公子好久不见,阿笑眼花缭乱,被姑娘们拥了,左搂右抱胡乱亲着,正拿不定主意找谁,忽抬头看见二楼站个女子,顾盼销魂,风情万种。
阿笑一个箭步冲上楼,对那女子赖笑道:“姑娘在等我吗?”柳暗殇忽见个男人扑来,吓了一跳,阿笑没等她反应过来,便一把将她揽进房里,关上房门。老鸨在楼下见了,笑道:“许营长的局,也有人敢抢,真是先到先得。”阿笑进到房里,把外衣脱下,往湘妃榻上倚了,忽觉屁股辣痛,起身欲解腰带,柳暗殇吓得忙摆手道:“大爷进错了房吧?”阿笑道:“没错,今晚就找你了。”柳暗殇道:“我今晚约了别人了,还请大爷见谅。”阿笑道:“别人不是没来吗?”柳暗殇嫌道:“我与大爷不熟,不好这样。”阿笑道:“过了今晚,自然就熟了。”柳暗殇道:“没见过大爷这样的客人,刚见面就色急成这样。”阿笑屁股痛,顾不上解释,正欲解裤,柳暗殇大叫道:“大爷不可,我还是叫妈妈给你另找一位姑娘吧。”说罢抢先一步,推开房门,冲出去对楼下的相帮喊道:“有位客人走错了房,快扶他出去。”鸨母在楼下幸灾乐祸道:“进了你的房,就是你的客,你就好生伺候吧。”柳暗殇急道:“可今晚是许营长叫的局,我正等他呢。”鸨母道:“你又不是许营长夫人,他来了自有别的姑娘接待。”阿笑也从房里出来,拦腰抱住柳暗殇,就往房间里强拉,柳暗殇手抓雕栏,口中连声惊叫。
话说柳暗殇叫声惊动街上一人,此人正是三刃木梁尘。她离了吉庇巷,往南一路追到下杭街,正愁没有线索,忽闻杏花天里嘈杂,有人喊叫,进门一看,见楼上阿笑对一女子施暴,气得攥紧双拳,后悔下午没把阿笑打死,大步流星冲上楼,抓住阿笑胳膊喝道:“撒手,放开她!”
阿笑复见梁尘,好似遇到了阎王,弃了柳暗殇不顾,抱头窜入房去。梁尘伸手去扶惊叫的女子,本想好言宽慰,孰料伸手一搭,觉那女子骨骼奇硬,心中暗叫不好。柳暗殇摆脱阿笑纠缠,刚松口气,忽觉一只手,十指纤长,搭在自己肩上,回过头来,与梁尘四目相对,见面前男人,好似戏台上的周郎一般俊秀。
梁尘对女子道:“请进房说话。”柳暗殇只好随她进房。梁尘关上房门,转身对女子道:“真是天下尤物,怪不得能倾倒众生。”伸手指挑她下巴,柳暗殇拼死抵住,含羞道:“大爷客气了。”梁尘暗道:不把你揭穿,你以为人皆可欺。故意装了色相道:“那就陪大爷玩玩。”突然出其不意,伸手在女子酥胸上一捏,感觉衣下松垮垮,像塞了团棉絮,女子大惊失色。 阿笑见状大呼:“太学先生非礼了。”梁尘对阿笑道:“这就算非礼了?那要是我把她衣服扒光呢?”阿笑闻言,不敢相信这话出自梁尘之口,大张了嘴,像被人扼住喉咙,梁尘对柳暗殇道:“把衣服脱了,大爷要看你光着身子的样子。”柳暗殇见此情形,眼珠一转,突然投身到湘妃榻上,钻到阿笑怀里,大喊救命。
阿笑忽然胸中充满豪气,起身拦住梁尘道:“你想干嘛?你这假道学,白天装先生,晚上要当禽兽吗?”梁尘道:“你不是禽兽,来这里干嘛?”阿笑一时语塞,稍后道:“那也不能两男作弄一女。”梁尘道:“你先让她脱了看看,到底是不是你说的两男一女。”阿笑糊涂了,用手指着自己、梁尘和柳暗殇道:“你我是男人,她是女人,这房里两男一女,难道有错?”梁尘心道:这房里确是两男一女,但绝非你这傻子所想的那般。 阿笑对梁尘道:“脱也得男人先脱,正好让你看看,我屁股今天被你打成怎样!”说罢又要解裤带,梁尘怕阿笑鲁莽,抬手遮脸道:“你敢!”这一幕被柳暗殇看在眼里,嘴角浮出一丝冷笑,未被阿笑梁尘发觉,旋即消失,她在背后问阿笑道:“这太学先生同你什么关系?怎么他白天还打过你屁股?”阿笑头也不回道:“他白天把我屁股打肿了。”柳暗殇道:“那你俩晚上正好接着搞相公,姑娘我失陪了。”说话间从背后将阿笑猛一推,阿笑站立不稳,迎面朝梁尘撞去,梁尘伸手将阿笑扶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