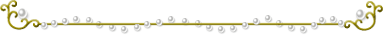
李娟 蝗灾
蝗虫来了。
他们说蝗虫来的时候,跟沙尘暴似的,半边天都黑了,如乌云密布,遮天蔽日。人往重灾区一站,不一会儿身上就停满了虫子,像穿了一身又硬又厚的盔甲。
那情景是我没有见过的。
还有这么一个数据,说今年闹蝗灾的地区,最高虫口密度为一万五千只/平方米。这也是我没见过的。想想看,一个平方的面积里居然能挤下一万五千只蝗虫!那肯定是虫摞虫了,而且还会垒得很高很高。一个平方一万五千只!真恶心……他们怎么算出来的?难道还一只一只地数过吗?真恶心……
为了抵御这场灾害,政府号召灾区群众多养鸡。有人告诉我,养鸡灭蝗的事情还给编了新闻上了电视呢。画面的大概情景就是:村干部们全体出动,把一群鸡从山上往山下呼呼啦啦地赶,鸡们纷纷展着翅膀,光荣地浩浩荡荡冲向抗灾一线。
哎!肯定吃美了!
可惜,那幕情景还是没有亲眼见过。
说到养鸡,想起了另外的一件事。十几年前塔克什肯口岸刚刚开关的时候,我的一个表姐也去那里做生意了。我和我妈便跟着去瞅了瞅热闹。在那里,政府要求当地群众积极参与贸易活动。提倡的办法之一也是号召大家多养鸡,因为鸡下了蛋就可以用鸡蛋进行边贸互市了。另外,还可以把鸡做成红烧鸡卖给外国人吃。可能蒙古国那边只养羊,不养鸡吧……
呃,回过头来再说虫灾。那么多的虫,鸡能对付得了吗?一个个吃到撑趴下,也是趴在虫堆里吧?那么多的虫——每平方一万五千只……太可怕了。
不过用鸡灭蝗好歹属于生物技术呢。听说还有的地方在喷药。喷药当然会更有效一些,但那么做总让人感觉不舒服:“药”比蝗虫更可怕吧?因为它实在太“有效”了,全盘毁灭一般地“有效”,很不公平地“有效”。
我们在深山里的库委牧场,离灾区还很远,但也能明显地感觉到蝗灾的迹象。尤其是前山一带地势坦阔的地方。往草丛里扔一块石头,就像往水里扔一块石头似的“哗啦啦”溅起一大片。在又白又烫的土路两边,一片一片全是黑乎乎的东西。开始还没在意,后来不小心踏上去一脚,踩死一大片,才知道……
我们这里的小孩子,钓鱼用的饵全都是蝗虫。不知道这有什么好吃的,鱼居然也能给骗上钩。
我记得小时候,还在县城里上小学时,我经常穿过整个县城去到北山脚下找一个叫玲玲的女孩玩。她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叫霞霞,一个叫明明。她家的房子很破,很空,但是很大。院墙从南到北、山上山下地围了一大圈,差点儿就无边无际了。她们的父母总是不在家,我们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地玩。后来我们跑了出去,外面是成片的戈壁滩、起伏的粗砾沙丘。我们四处捡拾干牛粪,拾回来可以当柴烧。因为她家很穷。穷人就烧这个,富人则一年四季都烧煤。我们去了很远很远,远得快要回不来了。后来我们回来时,红日悬在山头,晚霞辉映大地。我们放下牛粪块,开始捉蝗虫玩。那么多的蝗虫,那个时候就已经有那么多了。
——我们轻轻地走上前,轻轻地蹲下身子,突然罩上手,一下子就逮住了。捂在手心的虫子仍虚弱地挣扎着。因为它是活的,有生命的,于是捏在手心里总是令人异样地兴奋。它的腿能动,关节灵活;触须虽然看来和麦芒一样,但却是有感觉的,是灵敏的,再轻微的触碰都会使它迅速做出反应;还有它的翅子,那么精巧对称……对一只蝗虫仔细观察,从寻常中看出越来越多的不可思议时,世界就在身外鲜明了,逼近了……我看到玲玲的眼睛闪着瑰丽的光。抬头一看,绯红的夕阳恰在此时全部沉落西山,天色迅速暗下来。一回头,一轮大得不可思议的金黄色圆月静止在群山之上。
蝗虫是有罪的吗?作为自然界理所应当的一部分,它们的种种行为应该在必然之中:必然会有蝗灾出现,必然得伤害人的利益以维护某种神秘公正的平衡。当蝗虫铺天盖地地到来的时候,我们为保护自己而使用的任何方法,其实也是对自己的另一种损伤吧?
唉,我们这个地方农牧民真倒霉:不下雨的时候总是会闹旱灾,雨稍微一多又有洪灾;天气冷的时候有雪灾,太热了又有冰雹灾;秋天会有森林火灾,到了夏天呢,看看吧,又总是有蝗灾。此外还有风灾啊,牲畜瘟疫啊什么的。然而尽管如此,还是有那么多的人愿意在这里继续生活,并且也不认为受点天灾有什么太委屈、太想不通的。蝗虫也愿意在这里生活呢,草地一片一片地给它们咬得枯黄,于是羊就不够吃了。蝗虫真可恨,但也可怜。因为它们的初衷跟羊一样,只是找口吃的而已。
比起蝗虫,羊群的规模更为庞大,并且发展态势更是不可阻挡。我们所有的行为都向羊的利益倾斜,其实是向自己的利益倾斜——我们要通过羊获得更宽裕的生活,什么也不能阻止我们向着无忧无虑的浪费一步步靠近。我们真强大,连命运都能控制住了。
蝗虫来一拨,就消灭一拨。我们真强大,一点儿不怕它了。
可是,这是不祥的……因为蝗虫仍在一拨一拨地继续前来,并且越来越难以对付(名字也越来越神气,什么“亚洲飞蝗”啊,“意大利蝗”啊……)。自然界的宏大程序继续有条不紊地一步步推进,无可抗拒。尽管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感觉不到,只能以本能的敏感去逼真地体验些什么。
只知道,“更多的那些”,已经不像蝗虫那样好打发了。又想起童年中的玲玲和明明。此时,不知她们正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里平凡地生活。已经完全忘记了过去那些蝗虫的事情,一日一日地被损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