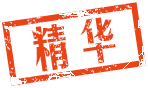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闷油瓶 于 2015-9-20 16:48 编辑
总是借着各种由头怀想从前,但其实也不是每个人的从前都有一些好的回忆可想,但怀恋旧时光和缅怀青春是地球人通病,谁都不能免俗。
好像大多人美好纯粹的感情都是在童年和校园的时光里,但仔细搜寻下记忆发觉,自己并没有。好像没怎么纯真过,就长成了浑浊的成年人,一身疲惫,满脸沧桑。习惯把人事都朝着最险恶思量,时刻做出防卫姿态,能够接纳的人很少,孤独但自己并不觉得,像只被遗弃 过的猫。
自己的童年里都有些什么呢?肯定没有一个属于小女孩的洋娃娃,从未有,那段记忆是空白的,也许是那时候的小孩子都没记忆,也许是自己没想记着就真忘了,反正啥都没有,好像被很突兀的剪掉了,连掩饰剪掉的痕迹都懒得掩饰。
念小学呢?各种动荡流离,在不同的学校辗转迁徙,还没有跟同桌熟悉,就又转学了,所以说起同学和校园,似乎大多记忆都在小学三年级之前,记得遮盖起试卷不让同桌抄的白报纸;记得班上第一个买了自动铅笔的男同学叫小明 ;记得校园花坛里女孩子们拿来染指甲的凤仙花;记得冬天来临前所有班级在操场上开去山上捡柴禾过冬的动员大会;记得大雪后清晨扛着自家的铁锹扫帚去学校清扫教室前的积雪;记得教师办公室房后那块雕刻花纹的石碑,村里人说这学校以前是个庙呢;记得冬天午休放在火墙上保温的铝饭盒,虽然只是玉米和咸菜,但好像比在家里吃的时候香甜了许多;记得每次收学杂费时的窘迫;记得后操场上的双杠和后来被拆除的秋千架;记得一场重感冒后无缘参加的运动会;记得小表姐去乡里参加珠算和速算比赛;记得大表姐背着自家缝制的布书包骑着永久自行车在冬天结成冰的路上去上学,记得她喜欢写钢笔字的时候拿格尺管束那些字站成行;记得表哥从关里回来时满口的山东话;记得育红班里曾经有一盒七巧板的积木;记得有一次考试1+1我抄了别人写的答案2;记得每次成把买回来的铅笔都被我在写字的时候咬的没有头;记得入少先队时是自己代表去宣誓;记得靠着东山的大河清澈见底,夏天的时候拿上陶瓷盆去河边洗衣裳;记得河边青青草地上都是晾晒的衣衫;记得洗完了衣裳在河里扎猛子比试谁更能憋气的自己;记得河水居然比岸上暖;记得泡在河水里太久嘴唇冻成的白紫色;记得每次顺着河水往上游走,拿着盆轻轻的放在河底石头边上,再翻开,偶尔会有小鱼慌不择路跑进脸盆里;记得舅妈家屋后那几棵李子树;记得姨娘给自己做的炸茄盒的味道;记得和小伙伴玩过家家时玻璃划破膝盖流了很多血;记得班主任喜欢的那个很漂亮的女同学。可为什么没记住那时候身边小伙伴的脸呢?老师、同学、邻里,那些脸怎么就都模糊了,像梦一样,隔着一层纱,天性凉薄吧。
初中是在山东念的,那段回忆里,关于学校和同学的,所剩更是了了。每天似乎除了值日生打扫教室,全体都要出操,然后是两节早课,等下课也不过八点,然后去吃饭。有寄宿,但自己并没有。漫长的一天,结束是在俩节晚自习后。回家骑着自行车走十几里路,并不觉得辛苦,有时大月亮地,觉得这天地似乎都是自己的了,没有恐惧,没有忧愁,很平静,很安心。那时候算是个过客,无法融入,听不太懂方言,还有对未来的不知何去何从的焦虑,但自己似乎并未明白这种焦虑,只是剪了很短的头发,像个假小子,没有同类。唯一的温暖是地理作业上来自曾经教导过自己的一个姓朱的男老师的批语,他说怎么偏科这么严重?后来课下在校园里遇见,老师很是忧愁的询问,怎么数学和语文差那么多?这样不行啊。他曾经教过我,是位代课老师,我是他任课时候的班长,初中地理课的课代表。觉得那是那段时光里极少的光亮,除了朱老师,没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偏科这么严重,为什么数学考成那个样子。而今,我却只记得他的样子忘记了他的名字。为什么只记得他的样子呢?我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也许潜意识里自己把对父爱的那种向往移情到了他的身上,因为他的那句批语,想着倘若父亲爱我,也会在自己学习退步的时候这样训斥自己。
没有夕阳下的奔跑,那不是我的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