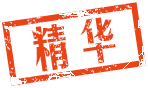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介入 于 2014-10-21 18:10 编辑
来路不明的跳绳3
我的目光绕过川爷跟贱人的腿,触碰到探着头朝我这边张望的卡卡,卡卡的神情看起来有点得意,我甚至能感觉到他眉毛轻轻上挑了两下。亲爱的卡卡,如果你有手,会不会此刻给我打出个大大的“V”字,我喜欢你卡卡,看到你,我觉着我拳头都握不紧了,指尖上都是温柔。
谢过川爷,走出他的店,贱人问我要去哪,送我,然后说要去参加朋友的婚礼,我说忙你的,我回我妈家,不远,可以走回去,我也想一个人走走。贱人没犟。
一进家门,我疲倦地坐进沙发里,拿起妈妈的茶杯喝了几口茶。 “你昨天在家忙啥?”姐问。 “没啥,写了个鬼故事。” 姐很明显的不高兴“告诉你,不许写了,身体不好,注意着点,还写什么鬼故事。”
我没说话,也不想说话,更没有把家里忽然多出来的跳绳的事告诉她们,一是怕她们担心,二是也实在疲于多话。 姐跟妈去厨房做饭,我躺在沙发里,回想着昨天的事,盼望天快一点黑下来,等晚上,等川爷跟卡卡还有贱人来我家,听川爷给我一个解释。我对时间有了期待。
吃饭的时候,我坐在自己固定的位置上,姐姐坐在我的右侧,期间,她不停给我夹菜,妈也跟我说,多喝点汤,看你那脖子筋挑着,看了都让人心酸。
吃过饭,我在沙发里午睡,昏昏沉沉的似乎又走进一个梦里,梦里,在跟一个男人激烈地争执着什么,我觉着我的眼睛往外喷着火,不停地撕打着那人,野蛮的像一头发怒的狮子,无法自控。那男人的脸是灰色的,我看不清他的五官,但心里隐隐约约知道他是谁,我很想看清楚自己到底是在哪,越想看清楚越看不清。 后来,我被那男人环腰抱住,我用力去掰他的手,怎么也掰不开,整个人被箍的死死的,他的手没有温度,胳膊很硬,硌的我生疼。
轻轻的敲门声,是梦吗,我想睁开眼睛,可怎么也睁不开,我觉着有人在推我,打了个激灵,人醒了,四周很静,妈妈在她房间休息,眼前的茶几上有摊开的报纸,水果,妈妈的花镜跟茶杯。
外边的天气已放睛,忽明忽暗的阳光透过窗玻璃,投在墙上一晃一晃的,像粼光闪闪的湖面。我能感觉到胸口有汗,额头上也是薄薄的一层。
晚上,我没敢一个人回家,我在约定的时间去了楼下,等川爷跟贱人,过了十分钟,或者更久些,他们来了,贱人走过来问早来了?川爷还是没有说话,牵着卡卡头里走,卡卡像是轻车熟路地带着我们上楼。 拿出钥匙开门的那一刹那,我感觉脸上的肌肉跟心脏同时抽搐了一下,我没敢先进门,更没敢用手去触摸墙壁上的开关,贱人问,开关在哪?
开了灯,川爷跟卡卡各个房间里转悠着看,我跟贱人立在门厅里,不敢乱动,也不敢说话,跳绳在哪屋,川爷问,我拿手指了指,跟着他去了那间屋子,奇怪的是,跳绳不在沙发的靠背上了,竟耷拉在沙发扶手上,一头快掉到地上了。我平时常躺在那里小睡,扶手被用来当枕头。 川爷眯着眼四处看了看,然后转过头问我 “恋爱过?” “嗯。” “后来呢?” “分手。” “为什么?” “他同时跟多个女人有染。” “然后呢,他人呢?” “死了。” “怎么死的?” “非命。被人拿绳子勒死的。” “知道了。”
你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你吸引而来的,你身体不好,就不该去那些阴气太重的地方,川爷说,不过你别害怕,没啥大事,他递给我一张符,告诉我临睡前放在枕头下,然后取出另一张压在跳绳上,冷冷地说“人作孽,不可活,赶紧的滚,像你这种傻叉玩意儿,我用小手指都能轻轻摁死你,如果下次再让老子看到你这垃圾,你肯定会别在卡卡的牙缝里,到时你的样子会比活着的时候还难看。滚!”我清楚地看到,挂在沙发扶手的红色把手轻轻来回晃悠了几下。 “卡卡,你留下,贱人,我们走。”说完川爷头也不回地走了,贱人回头看我,冲我眨了下眼,意思说安心睡。 我没有洗漱,一个高跳去了我的卧室,插上了门,把川爷给的那符塞到我的枕头下边。
这一觉睡得真香,好像我梦到了金黄色麦田。阳光浓烈。我还看到了大片的花海,振翅翩然的蝴蝶,翠绿的蜻蜒。还有潺潺的溪水。
睁开眼,天已大亮,我伸个懒腰,觉着脑子从来没有过的清醒,阳光照进来,秋日的阳光令人激动,有想哭的念头。秋天真是一个很大气的季节。敞亮。温暖。
起身,去了那边屋,拿起沙发里的笔记本,忽然觉着想起了什么,跳绳,一个叫卡卡的狗,可这念头只是一闪而过,我越想抓住它,它就跑得越快越远。
四下看去,什么也没有,一屋子阳光,线团儿正在埋头很认真的玩它的布老鼠,老鼠被它抓起来抛出去,看我进来,丢开老鼠迅速隐蔽在自以为安全的角落里,等我走近,便蹿出来抱紧了我的腿,顺势上爬,我轻轻把它摘下来,亲了亲,它的嘴,常年有鱼腥的味道,它细细的叫声,会令人产生对一些好日子的回忆和眷恋。
我打开电脑,去了论坛,想看看《老五来了》更新了没有。
完
告诉我,藏在我们生命的外衣下,活在我们心里的,这神秘的秘密,它到底是什么。作为一个结果的原因或一个原因的结果而到来的,到底是什么。这空前的绝望跟这莫大的解放,催促着我们的生和死,并由此而创造出比死更深刻,更生更神奇的梦,它到底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