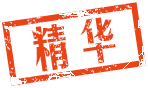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寂寞纱窗凉初透 于 2016-2-28 17:49 编辑
灯
初春的夜晚,微润的春意酝酿着丝丝清寒,昏黄的路灯把身影时而拉长、缩短,缩短、拉长,抬头看看绵延无尽的路灯,不知伸向何方,心底酸涩不已。
一座陌生的城市,一片陌生的心境——忧伤、无助、气愤。
想必此时的江南已经是杂花生树,烟柳画桥,游人如织了吧。校园里的九曲回廊定在碧如翡翠的清波上映出婀娜的身段;大片大片的山茶花,姹紫嫣红;莘莘学子的脸庞溢出对未来的憧憬,扬起的嘴角书写青春的骄傲。念及此处,悲戚的脸上露出一丝苦涩的笑意。
坐在被路灯晕染出层层橘色雾气的长椅上,我抚了抚包裹在长靴里的小腿,才发觉自己已经走了好久好久。环视四周,除了偶尔驶过的汽车,一片寂寥。刚刚分手的场景再次涌现,淡漠的眼神,冰冷的语言,潇洒而去的背影,似乎从来不曾相识,更从来不曾相爱。既然如此为何心痛到不能自已,或许是怜惜自己的真诚,感动于自己的感动,心痛于对方的冷酷无情。眼泪再次划过脸颊,不想擦去,就让自己任性一回,在静穆的黑暗中找到痛觉,寻回初心。
记得小时候,裹着小脚的奶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啥时候用上电灯,就好了。”奶奶对电灯的渴望伴随了我童年最初的记忆。
从我记事起就和奶奶生活在一起了,家里再没有旁人。平日里我总是看见奶奶用她那颤巍巍的三寸金莲,担着一根扁担,挑着两只圆底的铁皮小水桶去河边打水,她每次都要担上两个来回。因为她脚步的颤抖,总会溅出来一些水,抛洒在地上盛开出一朵一朵的小花。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脱掉鞋子,光着两只小脚丫去踩那些盛开的花瓣,乐此不疲。
到了晚上,奶奶会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做针线活。煤油灯燃烧的黑烟把小屋白色的墙壁熏染出了一个黑圆锥形的图案。煤油灯芯燃烧出一段灰烬的时候,我就会拿起剪刀,学着奶奶的样子去剪灯花。那时候不懂得李商隐“何当共剪西窗烛”的情趣,也不能体会“闲敲棋子落灯花”的雅情,有的只是希望煤油灯能再亮一些,让奶奶快快做完手里的活计,早点给我讲奇异的故事。那摇曳在遥远回忆里的煤油灯是童年的欢乐!
手机响了,瞥一眼,是刚才毅然决然分手的人打来的,懒得动弹,任由清脆的铃声回荡在耳边,路灯依然静默着,我把自己浸泡在这无边的静默中,路灯是孤独的见证者。
许多户人家窗口的灯相继熄灭了,起风了,春寒料峭的深夜,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我,第一次尝到了举目无亲,四顾心茫然的滋味,一个人的味道。
来这座城市之前,母亲一遍一遍地叮嘱:“好好相处,自己照顾好自己,不行了就回来……”当时自己还没心没肺地傻笑母亲啰嗦,现在呢?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罢了!一切随他去吧。闭上干涩的双眼,眼前却浮现出母亲坐在台灯前备课的模样,漂白了四壁的灯光将清瘦的母亲笼罩起来,描绘出“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的幸福,那灯光是亲人的气息。
相继几条短信出现在手机上,懒回顾。
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日子在痛苦中挣扎,为了慰藉心灵,只身来到神奇的西藏。
雪域高原的干爽、明净、清透、古朴、原始、寥廓,非身临其境者无法感同身受,往日来的阴霾一扫而空。看着虔诚的朝圣者,看着佛前跪拜的男女,听着喇嘛的经文,拨动转经筒,跟随大家齐诵“嗡嘛呢叭咩吽”六字真言,心境格外的平静祥和,灵魂轻灵了,升华了。跪在佛前点亮一盏佛灯,默念:我曾路过你的心,不是我不想停留,而是你不肯收留,此生无缘,愿你一生平安。
人人生而有爱,爱就在自己的内心,不是我们的爱错了,是我们看错了爱。我命定的那个人,不说他也懂;不是那个人,说了也没用;是那个人,不解释也没关系;不是那个人,解释也多余;是那个人,不留他也不走;不是那个人,留也留不住;是那个人,不等自然会遇到;不是那个人,原地也会走丢。每每默念那日的祝愿,忆及那盏佛灯,点亮一盏恒久的心灯,照亮自己,照亮别人,心若莲花处处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