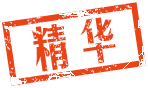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雪夜渔舟 于 2014-11-17 09:24 编辑
卿儿,对不起!在论坛里看到这个题目,情不自禁地,脑海中还是马上浮现出了你的影子。是啊,你在我的记忆里被尘封了三十年,每次在深夜里想偷偷溜出来,就被我强行按压回去。可是,这一次,我感觉我已经控制不住了,就像被按压的弹簧,总也会有个极限,在这一刻,心底最柔软的部分竟如刹那间决堤的洪水,呼啸着冲开闸门,将我溢漫,我不再挣扎,任凭记忆浸润开去……
记得是高二上半学期。
那天早晨走进教室,向自己的座位走去。班主任张老师正在黑板上写着什么。几个先来到的死党朝我挤眉弄眼、莫名其妙地笑着,啥意思嘛。来到座位旁,突然发现座位上多了一个女孩儿,穿着一件奶白色的连衣裙,皮肤比不上俺们的班花玲子白皙,运动头,额前齐齐的刘海,一双大大的眼睛,小巧的鼻子,看到我走到座位旁狐疑的目光,脸似乎有些红,拘谨地一笑,隐隐显现出两个酒窝。由于是坐着,看不出有多高,但据哥目测,应该在一米六三左右。奇怪了,哥也是班里的“问题学生”之一,前几任同桌因为被俺各种促狭溜之大吉,逃之夭夭,乐得我单独坐一张课桌快一个月了,做个小动作、翘个腿、睡个觉、下个位,那叫一个爽。看她笑得还算甜,便冲她微笑着点点头,风度嘛,总还要有的。其实,哥内心里知道,着实被她那双清澈的大眼睛震撼了一把儿。
后来,老师给全班同学介绍,才知道她叫杨子卿,是从四川宜宾转学来的,学习成绩在我们这个文科班算是中上等,但英语却是出奇地好,据“破锣”(班里的英语课代表罗勇)透露,水平和他不相上下。而且“破锣”诡秘地笑着说:“苗子,今后你的英语作业可有了着落了,别再来烦我。”NND,卸包袱倒挺快。
哥讨厌数理化,喜欢史地文,那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滴感觉多好,再看看那些学理科的书呆子,戴着比酒瓶底儿还厚的眼镜,整天就是抛物线、分子式(理科生表拍砖哈,嘿嘿),走对面镜片被太阳光一照,跟会车开大灯似地刺眼炫目,都不知走过去的是谁。但是,可但是,即使选择文科,高考时也逃避不了数学这一科,木有办法,天天可怜巴巴滴找“强子”(数学课代表,死党,班里男生的老大)要数学作业抄。说起来有些逆天,强子虽然也调皮捣蛋,但数学成绩超好,上课也不见他多么仔细听讲,有时还和玲子眉来眼去滴(见过他们偷偷递纸条),但下午自习课做作业时,只要看几遍例题,马上就能做出来,这数学天赋,不服不行。以前张老师曾经安排他和我坐一位,说是“一帮一,一对红”,俺也曾虔心地向他请教,刚开始,他也能耐心地说这一步要用到公式E,就能推出来下一步。可俺是求学务求彻底,于是问E这个公式从哪来的,他再接着上推到公式D,详细讲几遍,俺似懂非懂后,又打破砂锅接着问D公式怎么来的,他再向前追溯到公式C,如此这般推演到A甚至更早,他满头黑线滴对我说:“这些都是初中学的知识了”。有很多次因为追溯的太往前,最后都忘了原来要算的是什么。后来,他快要崩溃了,终于忍受不住俺的折磨,就差向老师跪求了,才换位走了。(不论怎么说,这也是俺曾经的一个同桌,虽然是男滴,但也符合题目,小小地回忆一下)
俺的数学是瘸腿了,毋庸置疑。英语呢,虽然也凑合,但成绩时好时坏,按张老师(教英语的)的话说那叫不稳定,记得有次考完试问他我考得怎么样,他直接来了句“流水落花春去也”,一个教英语滴,没想到语文知识竟也居然差不多能和俺媲美。这次,估计他也是想再提高一下俺的英语成绩吧,毕竟,能多一个考上大学的学生,老师脸上也更有光,奖金啥滴倒不像现在这么刻意强调,看来那时代的老师更多注重的是声誉,为国家多培养人才。不像现在,小学生要想当个班长,你懂滴。
再说了,班上当时一个人坐一位的也就两个,另一个是个女同学,坐最后一排,据说有肝炎,也不知是甲肝乙肝,反正是没人愿意和她同桌。剩下的就是俺了,加上俺其它科成绩还不错,能再提高下英语,高考的希望还是很大滴,恐怕这也是张老师让杨子卿和我坐一位的动机吧。
杨子卿比较文静,不是太爱说话,上课时认真的样子就像一个虔诚的教徒在听法师布道。说她不爱说话吧,但课堂上老师要下面学生发言时她举手还挺积极的。有时看她专注听讲的侧面,钢笔抵在下巴上,长长的睫毛,红润的脸庞,不时跟着老师的讲解会心地点头甚至报以微笑,心里都会想:她家里是干什么的?怎么会从四川跑到这里?细细地看也是很漂亮的哦,尤其是那双眼睛,可惜除了第一次见到我微微点头笑过外,就没再对我笑过。那时候不是太要求普通话,因此,课间听她和女同学说话时也偶尔蹦出几句四川话来,大部分能听懂,毕竟那时候老一辈革命家陈毅的电影、小说也没少看。
高中的生活单调而又丰富多彩,说它单调,那就是整天都是一节课连着一节课,那时候的家长不像现在的家长督促那么严,学好学孬,反正毕业后最差也能顶替接班,不愁没工作干。最开心的就是下午自习课后几个班之间展开的篮球对抗赛。课堂上奄奄一息的死党们在篮球场上可是生龙活虎一般,经常打得其它几个班轮流上。作为主力队员,球场上岂能少了俺矫健的身影?不过吧,有时只顾着打球,自习课都上不完就溜出教室,英语作业就让杨子卿帮我抄一下。刚开始她不愿意,斜着眼说:“自己做。”看她这么不识相,我就故意把屁股不断往她那边挪,她红着脸一个劲儿地往墙根缩,最后才轻轻地说:“平时你自己做,有篮球比赛时我帮你。”那也行,哥总算胜利了。
一次放学后,几个死党去天龙湖游泳,游完后上来,强子拿出一盒“淮海”牌香烟发给我们,然后龌蹉滴笑着问我:“进行得怎么样了?”我一愣,啥怎么样了?看我迷惑不解的样子,他说:“杨子卿啊,还没下手?可要抓紧哈,建哥(三班的老大)前两天问我杨子卿有主了吗,我说先帮着问问,看来‘来者不善’啊。你要真没那个意思,无所谓;要是喜欢她,可要先下手为强哈!”听强子这么一说,我倒平白紧张起来了,是呢,论长相,班里除了玲子外,杨子卿也算漂亮的了,别说三班的,就是破锣那几个家伙平时也都爱在杨子卿面前神侃,拼命表现自己,不就是希望引起她的注意吗?“近水楼台先得月”都没听说过吗?“肥水不流外人田”没学过吗?看来时不我待啊。我当时就对强子说,你对建哥说杨子卿已经是我女朋友了,强子坏坏地笑着答应了。
要说往女同学的茶杯里放个毛毛虫,在铅笔盒里放条小蛇,甚至在和我们男生作对的女生桌洞里塞几张中间染了红墨水的卫生纸(这是听老大的哥哥说的,当时不是太明白为啥这么做,只听说有特效)都没眨过眼,可真要是向一个女同学示好,还真没干过。毕竟哥平时内心里还是腼腆滴。于是请教强子(强子和玲子眉来眼去众所周知,至于有没有暗度陈仓不得而知,多年后问起强子,这家伙憨厚地笑着说惊天大案没做过,小偷小摸也难免,毕竟那个年代、那个年龄还不敢,此话我倒也相信),强子故作深沉,待我奉上一盒烟,然后帮他点着后,他才吐了一个烟圈说道:“很简单,七个字记着就行了,那就是‘胆大心细不要脸’!”想让他延伸一下其深刻内涵,他让我自己琢磨去,另外说可以买几本琼瑶阿姨的爱情小说看看,毕竟当时《一帘幽梦》、《秋歌》、《我是一片云》等书卖的很火,有一次我就在他床头就看到一本《梦的衣裳》。于是赶紧买了几本恶补了一下,果然觉得里面的故事又诗情又画意,又感天又动地,又可歌又可泣,就是情节忒狗血,这尼玛能用在哥泡妞上吗?
不论怎么说吧,反正从那以后我就刻意增加和她单独在一起的机会,很多问题懂装不懂地虚心求教,毕竟张老师对她说过要帮我把学习成绩提上一个台阶的。很多次近距离的接触,闻着她身上特有的那种淡淡的香气,经常会走神儿,而她,有时看我盯着她看时痴迷的样子也会借口去倒水赶紧走开。
元旦的时候班里按惯例都会举办联欢会,同学们把课桌移到墙边坐成几圈,中间空出一大片地儿表演节目,生活委员会买来很多瓜子、糖什么地小吃,大家谈笑风生,每个组轮流上去表演节目。当时很流行吉他弹唱,哥省吃俭用滴也买了一把,而且跟一个外面的朋友学过一段时间,经过一番苦练,记得左手因为按和弦都磨出了茧子,终于会了几个和弦,然后在那次联欢会上抱着吉他演唱了一首《少年犯》的插曲,听得同学们掌声四起。从那以后,发现杨子卿看我的眼神儿多了一份神采,我有时偷偷看她,她也会莫名其妙地脸红。每次打篮球时我也会发现场边多了一双关注的眼睛,回到教室的时候,也会发现杯子里的水都是温温的,刚好一口气喝完。不用问,我当然知道是她给倒的。她这是喜欢上我了吗?当时近乎弱智的我自然没分析出来结果。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几个死党晚上出去玩的时候都会喊上她,当然是放学时就约好了的,要不然晚上可不敢去她家喊她出来,估计她当时对家里也就是说出去晚自习之类的谎言。毫无争议的,我骑着自行车带着她,强子带着玲子,穿大街,过小巷(尽管我们用的是飙车的速度,可她在后车座上从来都没有搂过我的腰),破锣他们几个还没有目标,仍是光棍一条,只是跟着一起去热闹起哄,然后大家去小酒馆喝最便宜的“八五”酒,顾名思义,就是八毛五一斤的当地酒,饭后去湖边神侃,或者去公园抱着吉他弹唱当时流行的张行的一些歌。有时,杨子卿和玲子也会轻轻唱几首邓丽君的靡靡之音,让大家听得神魂颠倒。随着接触的增多,我也慢慢了解到,她原来是跟舅舅来到我们这里(他舅舅是在这儿做服装生意的),爸爸妈妈在家里有别的事顾不上她(后来才知道是闹离婚,怕影响她的学业)。
记得有一次玩到很晚才送她回家,快到她家门口的那条巷子时,她下了车,站在昏黄的路灯下,说她的眼迷了,让我帮她看看。我支起自行车,小心翼翼地扒开她的眼皮。其间,她仰着头,嘴唇离我的脸很近,呼出的气息如兰似麝,轻轻呵到我的脸上。一门儿心思找灰尘的我扒拉了半天啥也没看到,然后说:“啥也没有。”她这才掏出手绢揉了揉眼睛,默默地对我笑了笑,转身离去。
后来,我发现一首诗很符合当时的情景,那是舒婷的《会唱歌的鸢尾花》,诗中写道:在你的胸前,我已变成一朵会唱歌的鸢尾花,你呼吸的清风吹动我,在一片叮当响的月光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