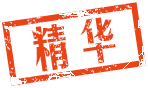老儒让阿笑坐下,故意不再提东坡,转而大赞李白,且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说得众院生个个强忍哈欠,眼皮半阖,老儒耳闻得课堂如太白墓般死静,知道需醒人耳目,便道:“诸位知《大鹏赋》不足,须知《临终歌》,知《临终歌》不足,又须知李阳冰,知李阳冰不足,又须知‘缙云飞声’,知‘缙云飞声’不足,又须知‘倪翁洞’,知‘倪翁洞’则必知‘铁线篆’。”院生们听到李阳冰之后,果然个个睁开眼睛。
老儒忽又来到阿笑身边道:“尔可知‘倪翁洞’不?”阿笑吓一跳道:“我只知道藏经洞,我在那里摔坏脑子。”众院生又即大笑。老儒又道:“那铁线篆想必会写了?”阿笑道:“见我爹写过”刚想说:“我却不会写。”被老儒一把将他拉到书案前,对大家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今日我等有幸见东坡后人挥毫。”阿笑推说不会,老儒当场笑道:“果然谦谦君子,足见深谙李阳冰《谦卦碑》精髓,六十四卦,唯谦一卦,六爻皆吉,快请,快请!”
诸位看官须知,这老儒铁线篆写得极好,故意让阿笑写字出丑,之后再自己写来炫耀。阿笑到了这个地步,只好硬着头皮,在书案上磨墨,一想到自己字如蚁走蛛爬,便满头冷汗,怕给祖宗丢脸,身体也颤抖起来,手中磨条把个砚台戳得笃笃乱响。
老儒知道阿笑不会写字,心中十分解气,嘴上却道:“古语曰:磨墨如病夫,把笔如壮夫。东坡后人磨墨小心翼翼,诸位要好好学了。”又走墨玲珑身边道:“若是颠倒过来,磨墨如壮夫,那写出字来一定如病夫无力了,呵呵”又自以为风趣,墨玲珑假装听不懂。
阿笑此时,忽然心生一计,趁老儒离开书案,把个树叶包从袖里掏出,倒出铁线蛇,扔到砚台上,搓面条般一滚,铁线蛇通体着墨,之后用毛笔尖挑了,放到宣笺上,对老儒道:“小生不敢卖弄,只写了一笔,还请师父指教。”说罢垂首站立一旁。
老儒闻言,飞步赶来,坐到太师椅上,只见书案宣笺上,一笔铁线篆,写得中规中矩,墨色饱满,笔画均匀,呼之欲出,比自己写了几十年的字,还要生动。老儒不敢相信阿笑年纪轻轻,有如此书法功力,但刚才只有阿笑一人,绝无代笔可能。待低头再细看时,那一划竟似活了一般,在纸上变换形状,老儒大惊,把个老花眼贴上去,不料那笔划从纸上伸出,爬到老儒鼻头上来,老儒“啊。。。。”的一声大叫,太师椅向后翻倒,四脚朝天,摔个仰巴攢儿,后脑壳碰在石砖地上“咣当”一声,晕了过去,鼻头被墨染黑,脸上像顶个煤球,颏下几缕黄须,像田里未收的枯玉米穗一样竖着。
座中几位姓梁,与老儒同宗的院生,赶紧跑过去,把老儒抬了,雇车送回家里。其余院生四散回房,阿笑本想偷梁换柱,应付写字,没想到事情闹得不可收拾,正惴惴不安,手臂忽被人抓住,阿笑做贼心虚吓了一跳,那人却大笑起来,阿笑再定睛一看,原来是墨玲珑,她问阿笑道:“你到底是怎么做的?把个老东西作弄晕了?真个解气,哈哈哈”阿笑怕被人听到,急忙去捂墨玲珑嘴,墨玲珑满心欢喜,愈觉得阿笑可爱,把阿笑挽着,将半个身子倚在阿笑身上,此举若在平时,定让阿笑有机可乘,此刻阿笑却两眼茫然,望着堂内壁上礼、义、廉、耻几个大字呆看,不发一语。
话说那老儒被人送回家里,抬到床上才悠悠转醒,家人把送他回来的院生围住盘问,院生支吾搪塞,只说个大致经过,家人听出老儒是在书院被人戏弄,以至于摔倒晕厥,不由得愤恨难平,欲找书院山长抓闹事的院生问罪。
话说此时后院竹林,有一女正在练拳,只见她一趟拳使下来,篁叶被她内力震得四散纷飞,稍后她收了拳,又从兵器架上,抽一把刀下来,闭目凝神,把全身内力运在刀上,另只手将一段枯木向上抛出,飞出竹林几十米,待落下与肩平时,迅疾出刀,只三刃将枯木砍成齑粉,落地无声。
之后女子将身上粉尘掸了,把刀还归架上,往前院人声嘈杂处一看究竟。此时前院佣人正传老爷在外面被人欺负了,晕倒不醒,被人抬回家里,女子见姨母从房里出来,满面泪痕,被几个书生模样的人劝慰,便一言不发,转到自己屋里,开箱取了一套男装穿了,束发成髻,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副假胡须,对镜粘在脸上,从后门溜出去,绕到正门对着的巷子里站了,等那几个书生模样的人出来,跟在他们后面一路来到书院。
这女子进了书院,直往山长室,山长恰好不在,她把室内墙上书院规则逐条看去,其中有如: 争讼 罚十五尺 嗜烟 罚二十尺 偷盗 除名 旷课 除名。。。。。 等惩罚条例都牢记于胸,之后转入空寂的课堂,把供案上一把海南黄梨木戒尺取下,凌空挥舞几下,觉得这戒尺坚硬如铁,如兵器般趁手,便逐渐加上力道,顿时一连串破空之声,女子脸上笑容刻毒,自语道:“没尝过三刃木梁尘的戒尺,岂能放你出鼓山书院的大门?”说罢将翻倒在地的太师椅扶起来,自己坐上去,屏息静气,等待下午小课。
诸位看官欲知这海南黄梨木戒尺,下午小课时要派什么用场,且听下回分解。